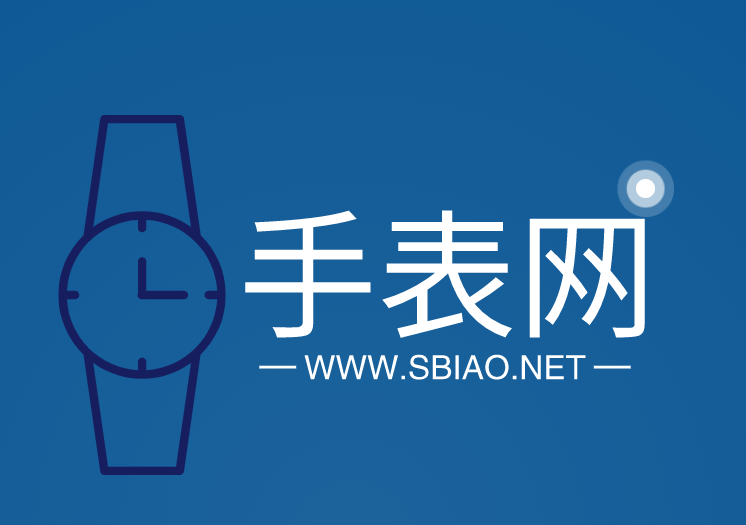东莞江诗丹顿手表维修店,给故宫钟表治病的“医生”

原标题:对时"上下三百年"给故宫钟表治病的"医生"
最近,一部叫作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纪录片火了,这部蹿红B站(著名弹幕视频站Bilibili)、高点击率高评分高弹幕的"三高"纪录片,不只赢了口碑、带热了故宫文物游,更引发网友对这群"身怀绝技"为文物治病的顶级文物修复专家的好奇与好感,这其中,文保科技部钟表组修复师王津师傅的人气尤其高。
"表白王师傅""为王师傅三刷""故宫男神"……五花八门称赞王津的弹幕满屏飞过,王津却感慨观众喜欢的其实还是钟表本身。16岁进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组,39年来专注于这一项事业始终如一,对于意外走红他显得羞涩,聊起钟表专业却侃侃而谈,"做了几十年,越来越喜欢,轻易放不开的。"
年轻人专门逛钟表馆 一眼认出"王师傅"
"没什么感觉,生活也没什么变化。"
随着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纪录片蹿红网络,王津也成了无数网友心目中"儒雅温润"的"故宫男神"。谈及突然多了好多粉丝以及在一众年轻人心目中的"高人气",王津羞涩地连连"否认","我觉得年轻人喜欢的应该还是钟表修复和演示过程的那个感觉。"
在王津看来,真正吸引观众的还是钟表本身,"原先对钟表不了解,来故宫甚至都不见得会到钟表馆转一圈,最多只是在钟表馆内看过静态的展示……"通过纪录片,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到钟表修复后的精致样貌,感受到它的魅力,王津感觉也不失为一件好事,"目前就是采访、爆料的比原来多了,我们这个行业或者说故宫修复组的关注度高了,也挺好的,关注钟表、钟表馆的人多了,知道在故宫除了中轴线,其实还有很多专馆都很值得逛一逛。"接受采访前一天,王津去钟表馆和同事检查某个钟表时恰好碰到两个年轻人,就是看了纪录片认出了"王师傅",也是通过片子对钟表馆感兴趣想来转转,"很年轻,来得也很早,故宫一开门第一拨观众进来看钟表。"
钟表走时功能基本大同小异,修复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各个钟表不一而足的表演演示功能,"成双成对都不一样,这个修复起来要比计时功能的难度大多了。"纪录片第一集片尾,王津看到全修复好、上满弦、演示功能全恢复情况下的钟表有感而发,"那种感觉跟不动的感觉就是不一样,感觉它就是一种活的状态。"王津解释,故宫里面的钟表不可能天天开动,否则会对钟表有一定磨损,一般就是修复好做静态展览,观众很少有机会能看到钟表修复好开动表演一刹那的样子,"这次院庆展那天,当时屏幕有个钟表动态的呈现,就是想让大家看到钟表修复后应该什么样,想想它们在钟表馆里天天静静地待着……看着都有点心疼。"
39年修了300件 已经"离不开"的工作
16岁进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组,至今39年的时间,王津没换过工作,甚至工作室都没搬过家,"就一直在这间屋,今年也许会有调整,新的修复中心落成之后,我们就要把现在所在的古建腾出来,搬到那一块儿,地儿大,环境也更好,不过估计也是下半年的事儿了。"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制片兼导演助理程薄闻对于和修复组师傅们共同生活的4个月印象深刻,"特别规律,师傅们每天早晨8点左右到,8点半打水陆续结束然后开始工作,一直到中午11点半吃午饭,之后一定要午休,下午1点多继续工作。"王津说午休已经成了他们一直以来的习惯,得到一定的休息才能保证下午的工作。
几十年的时光里,王津修复过的钟表大大小小约有300件。他直言,古时候的东西往往在细节上处理得可圈可点,"过去主要追求工艺细节,那会儿最多也就一对,不会批量生产,能做得更细腻、更经得起琢磨。"根据钟表大小及复杂程度,修复速度也不尽相同,"一般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都有,工艺相对复杂些的大型修复也有可能需要八九个月,最夸张的还有一年左右的,当然那中间也会穿插一些临时工作任务,比如说临时展览等等。"
纪录片中出现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,据王津回忆最初拿来时相当破旧,打开机芯看到里面的零件几乎都是拆散的状态,"估计过去的人修过,没修完又搁里面了,机芯零件拆完也没有还位,几乎是全放在里面把盖儿一盖,等于没修完就搁里了,至于为什么不得而知。"重新核实找回位置、坏的部分进行补配,这样才恢复成如今的面貌。对于王津来说,从事钟表修复工作这么多年,经验积累了不少,"基本一看大致的结构也能看出来,零件该归位的归位,该补的补。"
王津的师父曾经跟他说过,"要说真是干不下去了,干脆你就先到外面溜达溜达,转转,回来再干。"这句同样出现在纪录片中的话正是王津的切身体会。"有时候修复完了不管怎么调试都不转,走走停停挺烦的,就上院里转转,转一圈回来静下心重新找,看到底问题出在哪,这样的话反而便于你更快捷地找出问题症结所在。"王津强调,修复钟表的工作是个急躁不得、需要静心的事,"急了修不好,一个问题没解决还又造成了新的问题,得不偿失。"
用王津的话说,从踏入故宫开始,一来就接触钟表修复这行,他有兴趣,有耐心,还真没想过跳槽不干或从事其他职业,"也可能是环境决定的,到现在也觉得似乎就该这样一直干一辈子下去。"与其说对钟表的喜爱或是对工作的责任,王津倒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和习惯,这么多年的光景,离开已经不太可能,"做了几十年,越来越喜欢,轻易放不开的。"每天的工作状态看似周而复始,王津并不觉得重复枯燥,"最多'一对'才会出现一样的情形,大多数情况下每只钟表都形态各异,一般修复起来、演示起来多少都会有所差异。"
"匠人"巧遇"商人" 当时没感觉到摄像在拍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中老师傅和小师傅之间师徒如父子的关系也让不少观众津津乐道,比如被不少网友称为"偶像剧男主"的"昊楠哥"便是王津的徒弟丌昊楠。亓昊楠最初给摄制组工作人员的感觉也是"又酷又帅",程薄闻记得当时还是利用减肥话题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"亓昊楠给我看他的照片,两三年前他好像还是个大胖子!他告诉我减肥方法,后来每天就给我发信息,招呼我一起跑步,那时利用下午工间操时间两个人围着故宫跑一圈已经成了习惯,回来后再各自工作……"
在王津的心目中,集体培训可能更倾向于现代钟表那种程序化、统一机芯的职业需要,"同一个牌子的几个型号组装程序可能基本都一样。"古代钟表则不太一样,往往独立或者成对,"或许还是传统的言传身教更合适,我觉得是这样,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也是这样下来的,包括现在看来这个方法也的确是最可行的。"
程薄闻对于整个拍摄过程中在修复组感受到的亲切氛围回味无穷,"那么神秘的一个地方,你感受到的不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大师,反倒是一位位和蔼的老师,就是普普通通的人,很多弹幕说太像隔壁的大爷了,真的就是这种感觉。"王津坦言,修复组对外接触相对少一些,难免会给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,也会被猜测老师傅们的性格不如年轻人活泼,"我们这现在年轻人也不少,都挺好的,比如我们屋的小亓,包括屈峰他们,都是80后,跟这次纪录片摄制组成员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人,沟通起来非常方便顺畅。"
聊起这次拍纪录片的感触,王津感叹摄制组对细节部分的追求,"一点都不凑合,每个镜头都要做到最好,所以我们也尽量来配合,尽量不留遗憾。"有没有过畏惧镜头的时刻?"还真没有过,因为总体来讲拍摄的什么样,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就是这样,我们干我们的,他们拍他们的,互不影响。"
王津和徒弟丌昊楠去厦门出差参加钟表博览会的情节被网友奉为"经典","钟表匠人"和"钟表商人"的区别引发热议,王津的表情、语气也引来赞叹。"那次出差是当时摄制组知道后临时决定跟着我们前往,我们也是在展场转悠时碰到的黄嘉竹先生,就是很正常的接触,也确实是真实的记录,一点都没有摆拍,自然流露,自然对话。"王津笑言当时就是身上戴了个小麦克风,说话聊天会有记录,自己根本没太注意甚至没感觉到摄像在拍。"故宫怀表是有,但跟他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有,毕竟怀表种类太多,即便收藏再多也不可能将所有品种全收齐了,他有的故宫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。"
本站声明:本站内容来自互联网编辑转载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,请在30日内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。